info
資訊
黃宗潔書評〈那些雲端鑰匙也無法開啟之境──《苦雨之地》〉
「哈凡阿姨,你要不要到森林教堂走走?」
「教堂?現在?」
「對啊,現在。」
「有鑰匙嗎?」
鄔瑪芙很驚訝地看著哈凡。「森林怎麼會有鑰匙。」
(《複眼人》,頁185-6)
但凡熟悉吳明益的讀者,或許都會注意到他的作品之間,有時具有隱然相承的關係,比如《迷蝶誌》與《蝶道》、《本日公休》與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、《睡眠的航線》與《單車失竊記》。至於《苦雨之地》,則宛如那結束在反覆吟唱著「而一場暴雨,暴雨,暴雨,暴雨啊,一場暴雨即將到來」的《複眼人》之回聲──事實上,他自己也在〈後記〉中提及,書中第五篇〈恆久受孕的雌性〉與《複眼人》有關。不過,這部集結了六個短篇故事的小說,儘管在結構上非常精巧地設計為兩兩一組彼此相關,「彼處的峰巒是此間的海溝」(頁250),但若將全書視為一個整體,就會看出《苦雨之地》的企圖心,以及與前作的相關性遠遠不止於此。
一路從蝶道走來,吳明益早期的作品總被定位為「自然書寫」甚至「蝴蝶書寫」,身為一個不願被框限在固定類型中的創作者,他一直試著拓展寫作的疆界,無論《睡眠的航線》中的戰爭主題或《單車失竊記》開啟的物質文化史,都可看出他不願被定型的寫作態度。距離上一部可被歸類為自然書寫的《家離水邊那麼近》,轉眼已逾十年,因此,《苦雨之地》的出現,彷彿是一次朝向自然書寫的回歸與盤整。但這六篇小說,其實與他所有的作品共構出一個令人目眩的文學星系,它們各自獨立,卻又彷彿內建超連結般,有著彼此相連的線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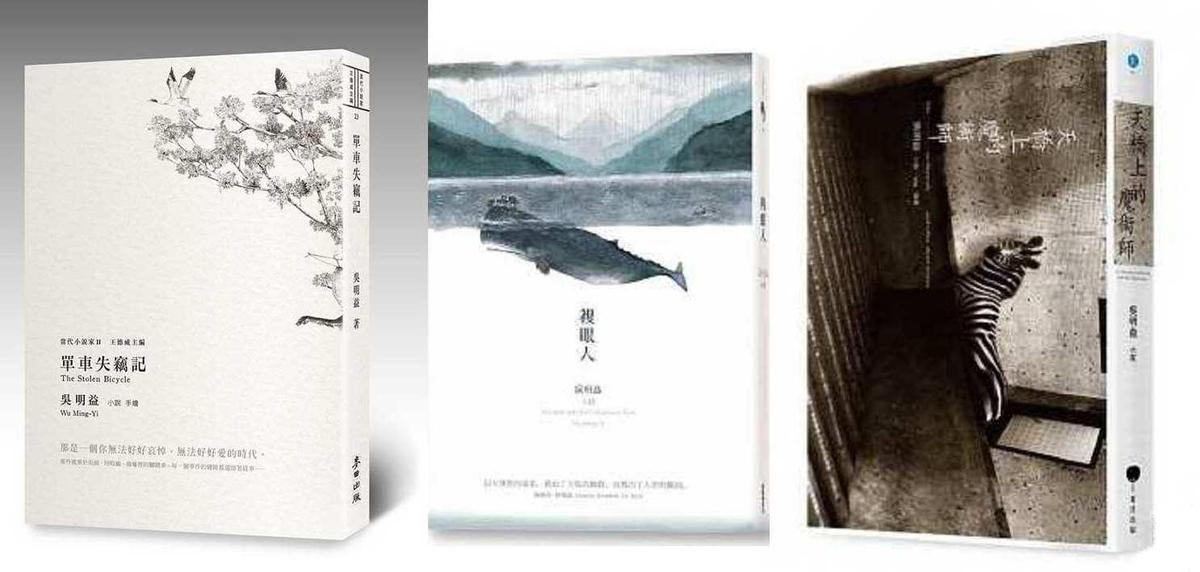
舉例而言,〈黑夜、黑土與黑色的山〉當中,小索菲的養父邁耶先生受困於島國的黑色山脈時,是「一位叫做達赫的布農人」將其從瀕死的夢境中喚醒(頁31);〈冰盾之森〉裡的敏敏在極地工作站等待時,閱讀的書單中有一本「阿蒙森(Roald Engelbregt Gravning Amundsen)日誌的副本」(頁80)──達赫和阿蒙森這兩個名字,想必《複眼人》的讀者都不陌生;至於〈灰面鵟鷹、孟加拉虎以及七個少年〉當中,舅舅那位「從來不開口說話,走路常常跌倒,但數理成績異常地好」的同學徐曜(頁229),則早在《虎爺》的〈夏日將逝〉一篇中就已登場,同樣是「啞巴數理殺手」、「總是低著頭,專注地看著地板走路」(《虎爺》,頁156)的形象;有趣的是,在〈夏日將逝〉這篇小說中,也已出現〈人如何學會語言〉裡的「雀斑」渴望開的那家「只能用手語的安靜咖啡館」(頁61)──那是一個以飛行為主題,畫著流動的雲,令人感覺微微暈眩的沉默空間,「一個暫時拋棄語言的空間」。(《虎爺》,頁191)又如〈冰盾之森〉裡的「意識情境治療」之於《睡眠的航線》、〈恆久受孕的雌性〉那句「人的身體裡有大海」(頁187)之於《家離水邊那麼近》……它們如同一個個「由此去」的標語,連接著通往前作的入口。
在小說中,鑰匙雖是病毒,卻帶有魅惑力
這些各自散發著光芒,彼此之間又彷彿有條隱形的線串連成星座的文本,與文學銀河系上的其他星體,更有著遙相對話的關係。我們不難看出吳明益的閱讀系譜中,那些對他而言具有啟發意義的作家──由他在小說出版後,所訂的講座主題已可略窺一二,其中包括艾加.凱磊(Etgar Keret)的〈謊言之地〉、安東尼.杜爾(Anthony Doerr)的〈獵人之妻〉、布魯諾.舒茲(Bruno Schulz)的〈鳥〉與〈著魔〉、博拉紐(Roberto Bolaño)的〈「目睭」席爾瓦〉、威廉.崔佛(William Trevor)的〈失落之地〉,以及勒瑰恩(Ursula Kroeber Le Guin)的〈大地之骨〉與〈蜻蜓〉。其中部分篇章在關懷的面向上,自有其鮮明的相通之處,例如〈人如何學會語言〉,可與《拾貝人》當中科學與直覺的辯證、以及對語言的思考並讀;勒瑰恩所建構的地海世界與《複眼人》瓦憂瓦憂島的掌地師、掌海師,則同樣召喚著某種遙遠的信仰……除此之外,《複眼人》中化身為鯨的瓦憂瓦憂次子們、〈人如何學會語言〉裡擁有「共感知覺」的狄子,亦可開啟通往尼爾‧蓋曼(Neil Richard Gaiman)或納博科夫(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)的「延伸閱讀超連結」,交織出複雜與流動的對話可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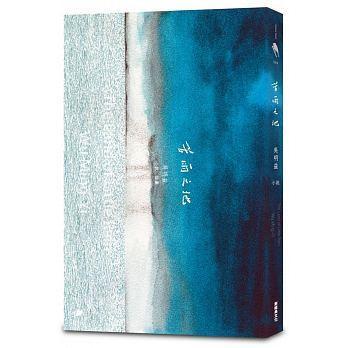
不過,若以《苦雨之地》作為認識吳明益的起點,亦無須擔心讀不出與前作相連的線索,會妨礙對小說的理解。這六篇故事自成一個完整體系,交織著類似的線索或關懷,既是兩兩一組,又彼此穿透,並以「雲端裂縫」此種電腦病毒作為串連的軸心。病毒在入侵雲端硬碟之後,會以大數據分析中毒者所有的數位痕跡,再將硬碟的「鑰匙」寄給某個「重要他人」。某意義上來說,我們或許亦可將《苦雨之地》視為閱讀吳明益作品的「鑰匙」,由此開啟他透過文學反覆思辨的若干課題。
在小說中,鑰匙雖是病毒,卻帶有魅惑力,不只是因為它總夾帶一個詩意的名字,而是你得以進入對方世界的「一切」,那些已知的事實與隱匿的秘密,從此一覽無遺。知道別人心中的秘密,有時是深具毀滅性的災難,但致命與吸引力本是彼此相依的存在關係。因此,〈人如何學會語言〉裡的狄子,甚至想要刻意讓媽媽的電腦感染病毒,好讓他能繼續和早已離世的媽媽,維繫著「對話」關係,並期待有一天能收到來自雲端的回音。〈雲在兩千米〉的主角「關」,更是因為檔案中妻子未完成的小說,而走上了追尋雲豹之路……小說主角選擇或放棄用鑰匙開啟他人封存的記憶,而走向不同的生命路徑;除此之外,裂縫病毒這個設計所帶來的科幻氛圍,更凸顯出作品背後的雙重特質──它既「科」且「幻」,同時包含大量科學知識、又不忘虛構小說的核心本質,而「雙重性」,或許正是來自吳明益作品的那把雲端鑰匙。
科學與文學、理性與感性、實證與想像、知識與詩意,在吳明益的作品中總是宛如彼此交織的雙螺旋,缺一不可,如同在《浮光》一書中「正片」與「負片」的設計;這也是何以前述的講座,他同樣安排「雙主題」的形式,除了短篇小說之外,各場皆搭配一個科普議題或作品,部分講題如「知識是小說感的肌肉」、「詩意的記錄與科學的記錄並存」、「自然史是科學與文學的共同領地」等,更可看出試圖兼顧兩者的寫作目標與態度。一如他在訪談時強調的:
「想像力是人類認識大自然的原始邏輯,加入經驗考證後便又回到紀實範疇,而人必然需於這種半實半虛的狀態下才能成長──努力去了解這個世界,對於不懂的事情有時仍可以乞靈於想像。」(註1)
「努力了解這個世界,不懂的事情則乞靈於想像」,這樣的信念在〈人如何學會語言〉可謂充分展現。從小對鳥鳴格外敏感的狄子,在失去聽力後試圖開發形容鳥名與鳥鳴的手語,在過程中,他發現許多生物學家對鳥聲的形容如此詩意,於是,他結合閱讀與創造,夜鷹的聲音成了「高處落下的酒」、黃鶺鴒的鳴聲是「掉落在草叢間的銀針」、黑枕黃鸝則是「水草在溪流中緩緩擺動」……(頁66)狄子讓我們理解,語言本身的侷限性及其超越的可能──就像〈冰盾之森〉裡阿賢的那句「不是所有的關係都會有名字」。(頁114-5)語言文字都有其難以盡意之處,但真正重要的是,如果失去感受與想像的能力,就算身為「明眼人」或「聽人」,也可能只是視而不見,聽而不聞。
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個顛覆了過往想像的「後自然」?
但是,在紀實與想像之間,科學與美學之間,它們彼此所信仰的價值系統之歧異如此巨大,我們有時遂不免在字裡行間感受到,相容兼美的理想背後,依然有其難以磨合之處。就像〈雲在兩千米〉的最後,他以神話敘事讓雲豹再現:「人獸交,才有神力,才會出現智慧,延續子孫。」(註2)至於基因工程這個選項,反而太過殘酷:「等到基因密碼都破解,有能力的人將耗鉅資打造完美的下一代,那是人類絕望的終站。」(註3)這篇小說對於神話力量的召喚,以及對基因科技的保留態度,毋寧相當耐人尋味。當科技無所不能,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個顛覆了過往想像的「後自然」?背後可能的代價又會是什麼?小說中不時出現這樣的遲疑。〈恆久受孕的雌性〉中,眾人費盡心力追尋神秘消失的藍鰭鮪身影,但如果最後找到的是一群仿生魚呢?這樣的尋獲「算是找到了,還是算沒找到?」(頁198)仿生魚是魚嗎?裝飾成彷彿活著的樹還是樹嗎?真與假、生與死的界線要如何區隔?一如菲利浦‧狄克(Philip K. Dick)那知名小說的提問:「仿生人會夢見電動羊嗎?」當人能創造萬物,我們會如小說中所引用的,發明第一隻機械鮪魚的提安達芬羅兄弟形容的那樣,「當機器鮪魚的設計愈來愈精細複雜時,我們就更敬佩活生生的鮪魚」(頁203)嗎?這樣的不確定感在小說中時而浮現。
另一方面,對科學知識的講究與細膩,卻又讓文學與想像在某些時刻彷彿是對科學的「冒犯」,就像狄子想要證明「鳥兒們自有自己的文化」(頁50),但他要面對的現實就是,承認其他生物可能擁有文化,是「一個鳥類學家無論再怎麼大膽也不會輕易提出的論斷」(頁50-1);有些時候,未經查證的文學想像甚至可能意味著某種誤導,例如「沙勒沙」這個角色,對琳達‧霍根(Linda Hogan)作品的評論:「在水底縫上鯨嘴以防鯨身下沉很有文學魅力,可能會有文學評論家努力解讀這個象徵,但實際卻是錯的。鯨的嘴並沒有通向肺,是噴氣口才通向肺。」(頁171)
這世界仍有太多我們知識與視域之外的未竟之地
然而,真正該問的問題或許是,感性與理性,我們非得二選一嗎?如果雲端鑰匙做為人類科技文明進展的某種象徵,這看似可以深入人的經驗與記憶極限的病毒,真正無法破解的痕跡,其實並非那些加裝了「滅跡」軟體(頁159)的電腦,而是人以外的世界,那些不曾被誰放在心上,或就算放在心上也無力改變的生物的境遇。雲端鑰匙沒辦法帶我們看到〈灰面鵟鷹、孟加拉虎以及七個少年〉裡,那隻先被關在永樂市場地下室,最後更悲慘的在街頭被公開肢解的孟加拉虎,一生中的每一天是怎麼過的;看不到灰面鵟鷹的下落;也看不到消失的藍鰭鮪哪兒去了。這是科技文明所能企及之地的極限與侷限。而那些雲端鑰匙抵達不了的地方,埋藏著更多生與死的痕跡線索,得用愛與感受去開啟。
因此,《苦雨之地》的六個故事始於愛,終於死,相信並非偶然。〈黑夜、黑土與黑色的山〉裡的小索菲,因為五歲時收到的那份「愛之土」,愛上從土裡孵化的小魚,進而愛上了泥土以及土中的一切生物。但是「加上水和愛的信念」(頁12)並不能保證牠們活下去,「在她的水族箱裡,那小規模的雨水和洪水都是她所創造、賜予,她的疏忽對牠們而言將是毀滅」(頁19);〈灰面鵟鷹、孟加拉虎以及七個少年〉的最後,舅舅在街頭看見了那隻他當年曾動念卻無力買下的老虎,他說:「如果那天那頭老虎還活著的話,不管千金萬金,都會把牠買下來。不過,牠已經死了。」(頁242)

「牠已經死了。」這不免讓人隱隱懷疑,科學與神話,或許從來都不曾指向救贖。神話救不了雲豹、救不了藍鰭鮪,也救不了孟加拉虎,科學其實亦然。它們指向的,毋寧是人心與人性。神話與科學,是人類試圖解釋世界的兩個方向、兩種信仰系統,但如果我們不願誠實面對人心,試著看見人的傲慢與侷限、人的努力與彌補,將沒有任何路徑可以通往救贖。如同吳明益在〈後記〉中所引用,麥卡錫(Cormac McCarthy)《長路》裡的那段話:「時間,時間裡沒有後來,現在就是後來。」我們此時此刻作的一切,就是後來。
而《長路》這部小說的結尾,或許亦可借以作為《苦雨之地》的某種旁注:「深山溪谷間曾有河鱒,在琥珀色流水中棲止,……魚背上彎折的鱗紋猶如天地變換的索引,是地圖,也是迷津,導向無可回返的事物,無能校正的紛亂。河鱒優游的深谷,萬物存在較人的歷史悠長;它們輕哼細唱,歌裡是不可解的秘密,晦澀的難題。」這世界仍有太多我們知識與視域之外的未竟之地,太多無可回返的事物與不可解的秘密。自然沒有鑰匙,我們只能循著生痕與獸徑,試著接近那無可回返的曾經。
註釋:
本文作者─黃宗潔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、國文學系碩、博士。長期關心動物議題,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。著有《生命倫理的建構》《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──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》《牠鄉何處?城市‧動物與文學》《倫理的臉──當代藝術與華文小說中的動物符號》。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。
